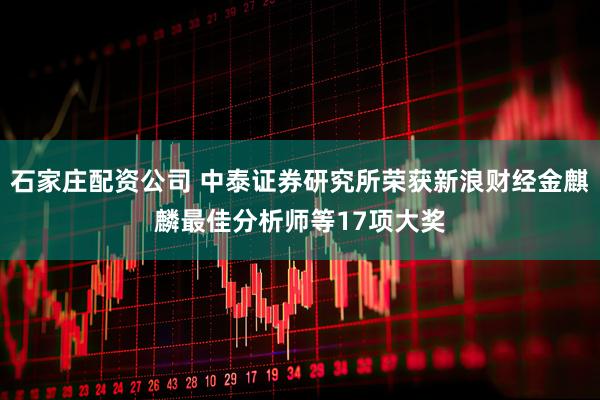十年前石家庄配资公司,一个长期活跃在开源社区、用着 Mac、还对"大厂文化"心存戒备的工程师,做出了一个令朋友们意外的决定——加入微软。
如今十年过去,他依然在微软,并于近日写一篇《在微软的十年》的思考及回顾文章:从 Azure 的起步到当前生成式 AI 的浪潮,从企业文化的变迁到个人生活的平衡,这既是对职业生涯的复盘,也是一个老派工程师与时代变化同行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这篇自述,看看这位亲历者眼中真实的微软十年。
作者 | Rui Carmo 责编 | 苏宓出品 | CSDN(ID:CSDNnews)
自从我加入微软,已经十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记录一下做一些纪念,所以现在也不例外。

初加入微软
你可能会好奇,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像我这样的人——对技术持开放态度、长期参与开源项目,同时还是 Mac 用户——当初想加入微软的理由,对一些朋友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许现在依然如此)。
简单来说,当时的我在电信行业干了十五年之后,看到了一个机会:参与"下一个大事件"(也就是超大规模云服务的发展)。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一切其实在我加入前一年就有了开端。虽然早些时候就有熟人在那边私下联系过我,但直到下面这件事发生,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面对的是多么大的文化转变:

原始幻灯片已丢失,但这里有一个重新制作的版本
一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冒险一试。
实际上,我很惊讶自己竟然在微软待了这么久。这并不是因为微软最近经历了几轮裁员(我曾一度担心自己快要被裁了),而是因为我原本以为云计算的普及会像典型的五年周期的范式转变那样渐进。
简而言之,微软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我见证的不仅仅是一次范式转变……

时代之旅
回顾在微软的过去十年,我通常会把它划分为五个鲜明的时代:
Azure 及其首批重大部署 —— 企业逐步采用、数据中心扩张、新服务和功能陆续上线的那些年。
云分析 /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 随着人们在 Azure 上构建更复杂的应用,这些技术逐渐走到台前。
Teams —— COVID 带来的最大遗产,不需要多说。
战略性的绕行与回归电信根基—— 但随着 Azure for Operators 的关闭,这段经历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生成式 AI 带来的巨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 Azure 的关注,把焦点重新转回终端用户的生产力。
这些阶段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技术上的——我需要不断学习、适应,有时还要教别人。这些变化也影响了我每天直接共事的人,以及覆盖到了本地或全球业务区域,也对我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幸运的是,我在学习新技术或根据需求调整工作重点时都没有遇到问题——我已经习惯于在一天之内同时应付安全、深度机器学习、项目管理、DevOps、数据治理、物联网,以及 Python AI 框架的各种复杂细节问题。
但我并不完全满意于自己成为一个"万能技术通",因为我真正热爱的,始终是构建东西。

永远被工程与业务夹在中间
此外,我目前的角色和头衔(高级项目架构师)有一个明显缺点:它让人很难看出我这些年在公司内外带团队、管流程积累下来的管理经验。所以,每当要向"圈外人"解释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场面总会有点尴尬。
而且,我渐渐意识到,不论是工程组织还是整个就业市场,对拥有"架构师"头衔的人通常并不看好。
相信我,"架构宇航员(architecture astronaut)"这个词并非凭空出现。世上有太多人会为了概念图争得面红耳赤,却可能一行代码都不写,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不去与人交流,理解真正需要做的事。
我理解这种偏见,也从不让自己的角色定义自己——而总是让自己做的事来定义我。

回顾往事
总体来看,如今的情况让我想起了 2008 – 2009 年我在 Vodafone 的经历。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次范式转变(当然,也包括一场泡沫),业务形态正发生快速而根本性的变化,各组织都在努力跟上节奏。
但与 Vodafone 不同的是,微软并不沉湎于过去,也毫不避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深度组织变革。

公司的变化几乎就在你眼前发生,至少每个季度都会有改变。
事实上,过去十年我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适应变化是一项关键技能,因为微软不断适应并为持续变化做规划。每年都会有变化(甚至每季度都有),所以不同于 2010 年前的日子,我既不感到无聊,也不觉得战略本身有根本问题(熟悉 Vodafone 360 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称之为"微型仆从效应(Microserfs effect)"(虽然今天的微软与那本书描绘的世界已大不相同),意思是微软之外的人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里的文化和节奏。

工作背景
我回到 Industry Solutions 部门(如果你在微软呆得够久,你可能还记得这就是微软咨询部门)已有一年了。能回到熟悉的同事身边,并在一个运作清晰、重点明确的部门工作(当然,组织重组允许的范围内),让我感到很满足。为客户构建东西,是继为自己构建之后的最佳体验。
与此同时,直到最近,我几乎没有与葡萄牙本地的工作有任何联系(除了生活在这里以外),过去七年我几乎只与海外公司合作。
这多少有些孤立感:我很少去当地办公室(现在这里的人远比以前少,更别提与我有共鸣的同事),我几乎没有葡萄牙客户(偶尔会与我合作的跨国公司本地分支有接触),而与我平常的工作环境相比,本地市场显得极为有限。
这也造就了一些宁静的时光——即便如此,有时我连享受房子都无心。
不过,我对七年前"离开"葡萄牙几乎没有遗憾,否则我无法学到这么多东西。
然而,回顾自己职业生涯中在葡萄牙创造的一些最佳经历(在 INESC、Telecel 以及后来的 Portugal Telecom),我总觉得应该以某种方式回馈,这个念头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
我有幸参与过一些投资和技术咨询工作,这似乎是回到葡萄牙的理智方式——即便很难找到真正能满足我使命感的事情。

泡沫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完全相信 AI 已经成为长期趋势,而且如果用得好,它能显著提升生产力。但那些以为 AI 会替每个人写代码、取代所有岗位,或者认为现有技术会像摩尔定律一样持续快速发展的想法,很快就会撞上现实。
而且,这个过程肯定会很痛苦。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概念产品演示(vaporware keynote)"的时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会像 2008 年那样崩溃。
我当然希望不会(我手上还持有一些股票,虽然不会改变人生,所以这里有一点自私的担忧)。但如果我在 NVIDIA 工作,我可能会更紧张,因为现在性能和效率的提升更多靠软件——比如模型设计、定制化方案和集成优化——而不是硬件,不管你在硬件上加多少花哨的特性。
我很确定,现有技术不可能产生 AGI(任何了解我们仍主要依赖蛮力计算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而一旦这种认知被广泛接受,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冲击。

行业格局
正如我去年写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并没有带来任何帮助。虽然行业对 AI 的未来还有一定回旋余地,但关税和经济不确定性仍在推动公司削减成本和裁员。

结合过去几年自己的经历,我确实会担心工作的稳定性——不管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如何,这也是我近年来在科技行业感受到的一个重要变化。
很多传统公司在 IT 领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无论是否转向外包),而一些专注的工程团队也减少了招聘。同时,我也听到更多关于年龄歧视和"消失招聘"(ghosting)的抱怨,因为 HR 招聘团队本身也在缩减。
所以,这不仅仅是 AI 的问题——更现实地说,公司是在降低未来员工成本的潜在风险。

个人生活
经过一年的自我调整、改进生活习惯,再加一次小手术带来冲击,我终于让自己找到了一种平衡感——短期的个人目标大体稳定下来,而我开始把健康与身心状态放在工作之上。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追求更高的成就,或者对新奇、有挑战性的事情失去了兴趣。只是这些事情并不完全由我自己掌控,而且比起每天保持清醒和活力,它们的重要性反而低一些。
所以,我的工作间隙大多变成了锻炼时间,这让我的心情好了不少。不过,这也没带来多少面对面的社交机会——毕竟,我的工作跨越整个 EMEA 区域,午餐时间被会议占掉,也很难在里斯本线下见到朋友或同事。
这大概是我目前职位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点。虽然我不介意比中欧同事晚下班,但会议时间常常和我的作息不合拍——最后经常妥协,为了开一些本来可以用邮件解决的会而跳过午餐。
不过,我还是能稳定地为自己的项目和兴趣腾出时间。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捣鼓工业硬件和电子设备,玩得很开心——哪怕很多时间都花在把机器学习塞进越来越强大的单板计算机里。
现在,用 CAD 设计东西,或者亲手造点什么,是我最享受的时刻,我偶尔也还会写点底层代码。

对我来说,硬件依然比软件更有趣。
谁知道呢,也许哪天我还能找到机会石家庄配资公司,重新投入到真正的产品构建中去。
恒运资本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